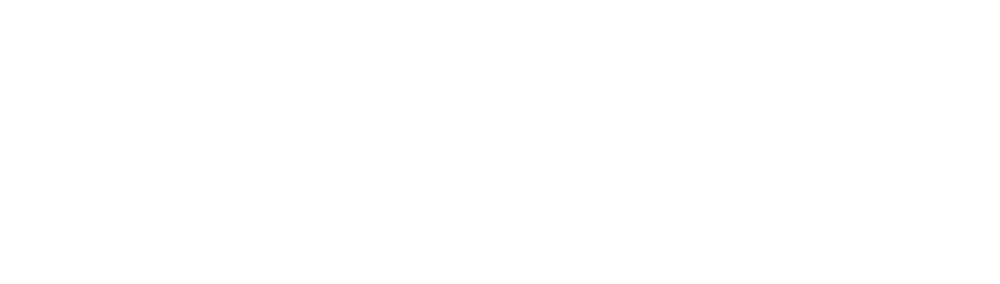

母语,往往被视为对一个人来说最亲切、运用起来最娴熟的语言,作家也不例外。大多数作家都是用母语写作,在自己最熟悉的字词之中探索新的表达。
熟练的双语甚至多语写作,是一些作家的额外技能点。出生于圣彼得堡贵族家庭的纳博科夫,早年写作过俄语小说。但他真正在文学和文体上走向成熟,却是到美国以后用英语写成的《洛丽塔》。早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者约瑟夫·康拉德其实是波兰人,他用英语写出《黑暗的心》《阴影线》等作品,让他成为“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”。荒诞派戏剧代表作《等待戈多》,是塞缪尔·贝克特用法语写成的,他本人其实是爱尔兰人。
美国当代作家裘帕·拉希莉也是一位精通多种语言的写作者。她出生于英国一个印度移民家庭,母语是孟加拉语,但她的处女作,“普利策文学奖”得奖作品《解说疾病的人》是用英语写成,这也让她迄今保持着该奖项最年轻的得主地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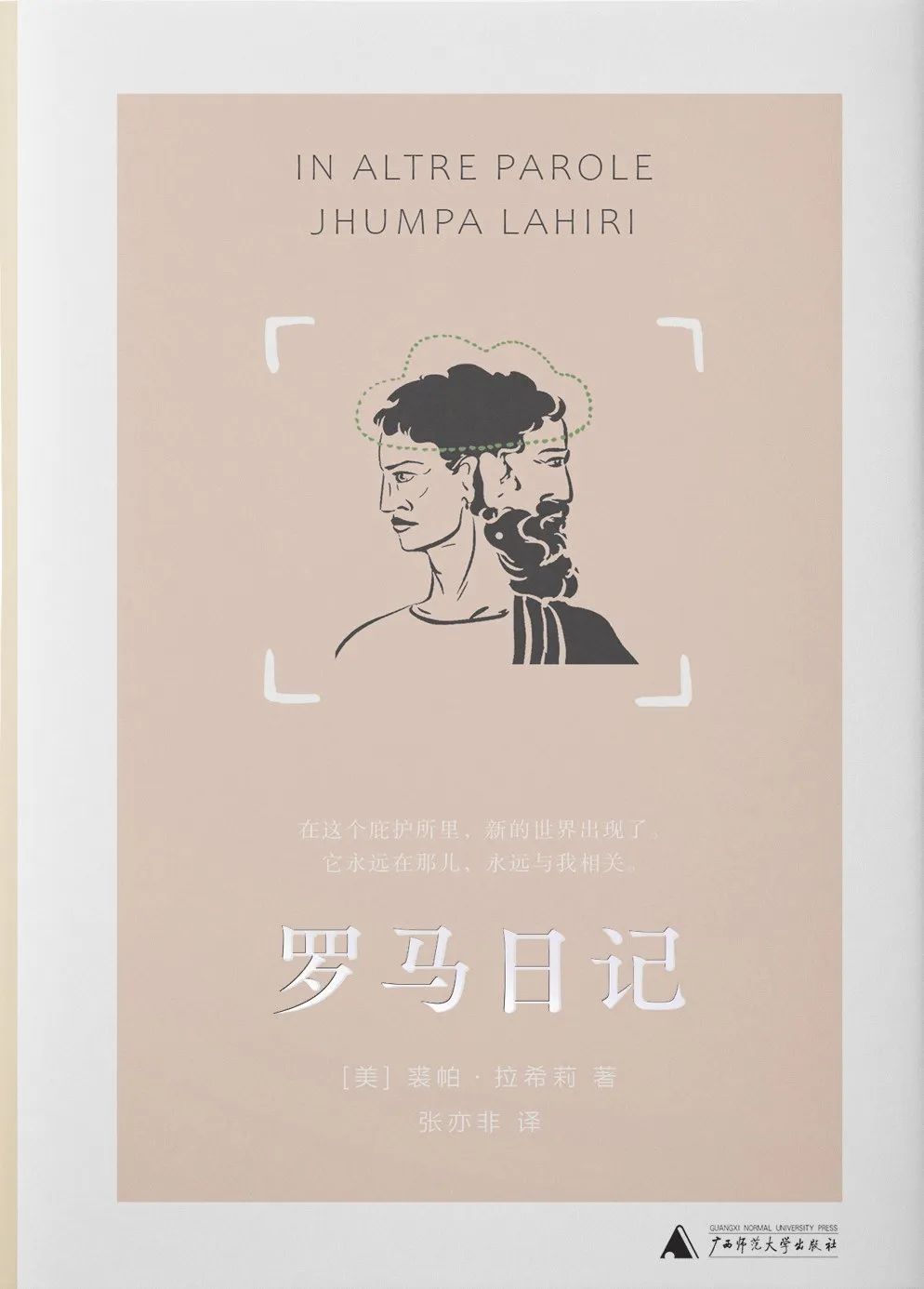

左:文库本《罗马日记》
右:曾获普利策文学奖的《解说疾病的人》
但她不止用英语写作,到意大利之后,她开始学习意大利语,尝试用新语言写作,《罗马日记》就是她用意大利语写成的自传性随笔集。其中包含她在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中求索的经历,她通过语言重塑自己身份认同的心路历程,被人理解与自我理解的“变形记”。“我用但丁的语言写作,以一种更纯粹的方式触及灵魂、触及我所处的现实。”精简雕琢的字句之间,是作为一个语言大师的成长之路。
“或许身为作家,我本就不完全属于任何语言吧。”泅渡陌生词语的海洋之后,身为作家的裘帕·拉希莉反而摆脱了语言的桎梏,获得了“不必完美的自由”。
或许身为作家,
我本就不完全属于任何语言。
有一个月了,我一直绕着湖游,从不往湖心方向去。我游的距离其实更远—圆周相比直径而言。得花半个多小时才能绕湖一周。我总在湖岸附近,只要累了就能站住脚休息。这的确是不错的锻炼,只是很难让人兴奋起来。
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,有天早晨我约了两位朋友在湖边见面。我已经下决心要和他们一起游到对岸,去那座小屋。我实在厌倦了在湖边游来游去。我摆臂划水,知道同伴们也在水里,但也明白我们仍是彼此孤立的。大约划了一百五十下,来到湖心,水最深的地方。继续向前。又划了一百下,终于重新看见了湖底。
这就到对岸了,好像并没有多难。我看到了那座曾经出现在远处的小屋,此刻就在几步开外。我看到丈夫和孩子们小小的、遥远的轮廓,仿佛难以触及,虽然事实并非如此。穿湖而过之后,已知的湖岸变成了对岸,此处变成了彼处。我觉得精力尚足,于是再次游到了湖对岸,倍感振奋。
二十年来,我学习意大利语的方式就像沿着湖边游泳,总是紧靠我的主导语言——英语,总是停留在岸边。这的确是颇为有效的训练,对肌肉和大脑有益,却难以激动人心。以这种方式学习一门外语,是绝不会溺水的,另一门语言始终在近旁支持你,随时可以相助。然而,安全地浮在水面上,排除了溺水和没顶的可能性,这还远远不够。要想掌握一门新语言,完全沉浸其中,就必须离开岸边。别穿救生衣。别依赖脚底的地面。
——《穿湖而过》

我多多少少已经习惯了语言上的流亡。在美国,我的母语孟加拉语是一门外语。你自己的语言在你生活的国家被当作外语,这会导致一种持久的疏离感。你在说一门隐秘的、不为人知的语言,它与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呼应,这种缺失会在内心造出一段距离。
对我来说还存在另一种距离、另一重分裂:我的孟加拉语不算好。我没法阅读,不会书写,说话还带口音,一开口总是底气不足。我感到与这门语言之间永远是割裂的。这样一来,非常矛盾地,我的母语也相当于外语。
至于意大利语,流亡有另一层含义。我和它几乎刚刚相遇就分开了,对它这样一往情深非常愚蠢,但我知道自己的感受是真实的。
怎么也会有这种流亡之感呢?我甚至不会这门语言,它也从来不属于我。或许身为作家,我本就不完全属于任何语言吧。
——《流亡》
在使用意大利语时,
我拥有不必完美的自由。
我发现,用另一种语言阅读比用英语更加私密,带来的感受也更为强烈。这门语言和我相识的时间还很短,我跟它并非来自同样的地方、同样的族群,我们没有一起成长。它并不存在于我的骨血中。我在被它吸引的同时也会感到底气不足。它仍是一个谜,被爱着然而无动于衷,在我的情绪面前没有任何反应。
那些不认识的单词总在提醒我,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
有时候一个词会引发奇怪的反应。比如有一天我看到“claustrale”(隐居的、与修道院相关的)这个生词,意思大致能猜到,但我想要确认一下。当时我正在火车上,查了便携字典,但里边没收录这个词。突然间,就像着魔一样,我坐立不安,非得弄明白它的意思不可。这念头荒谬至极,但我当时就是觉得:弄清这个词的意思可以改变我的生活。
毕竟,能改变我们生活的东西总是在我们自身以外。
——《借助词典阅读》

成为作家之前,我一直是缺乏清晰明确的身份认同的。正是通过写作,才感觉到某种自我实现。但用意大利语写作时并没有同样的感受。
对作家来说,在缺乏权威性的情况下写作意味着什么?如果感觉不到自己的可靠性,我还能自称“写作者”吗?
用意大利语写作的时候,既感到被钉在原地、受到限制,又好像更加自由了。这怎么可能呢?或许是因为在使用意大利语时,我拥有不必完美的自由。
考虑到我总是试图通过写作来破译一切,用意大利语写作,或许只是学习这门语言的一种更深刻、更刺激的方式。
自从孩提时代起,我就只属于我的词语。我没有所谓祖国,没有特定的文化背景。如果不写作,不和词语打交道,我就无法感觉到自己还活在世上。
一个单词是什么意思?一种生活有什么意义?到最后似乎是一回事。一个词可以有很多维度、很多细微的差别、极大的多样性,一个人、一种生活也是如此。语言是一面镜子,是最重要的隐喻。说到底,一个词的意义就像一个人一样,不仅无穷无尽,而且难以言喻。
——《脆弱的庇护所》
作为成年人,作为写作者,我为什么会对自己与不完美之间新的关系感兴趣?它能给我什么呢?我会说这是一种惊人的清晰感,一种更深刻的自我意识。不完美会激发创意、想象和创造力。它给人以刺激。我越觉得自己不完美,就越觉得自己活着。
我从小就开始写作,是为了忘记自己的不完美,为了把自己隐藏在生活的背景中。在某种意义上,写作是对不完美的额外馈赠。一本书和一个人一样,在整个被创造的过程中,始终是不完美、不完备的。经历了孕育的过程之后,人会出生,然后长大,但我认为一本书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才是活着的。写完以后,至少对我而言,它就死了。
——《未完成过去时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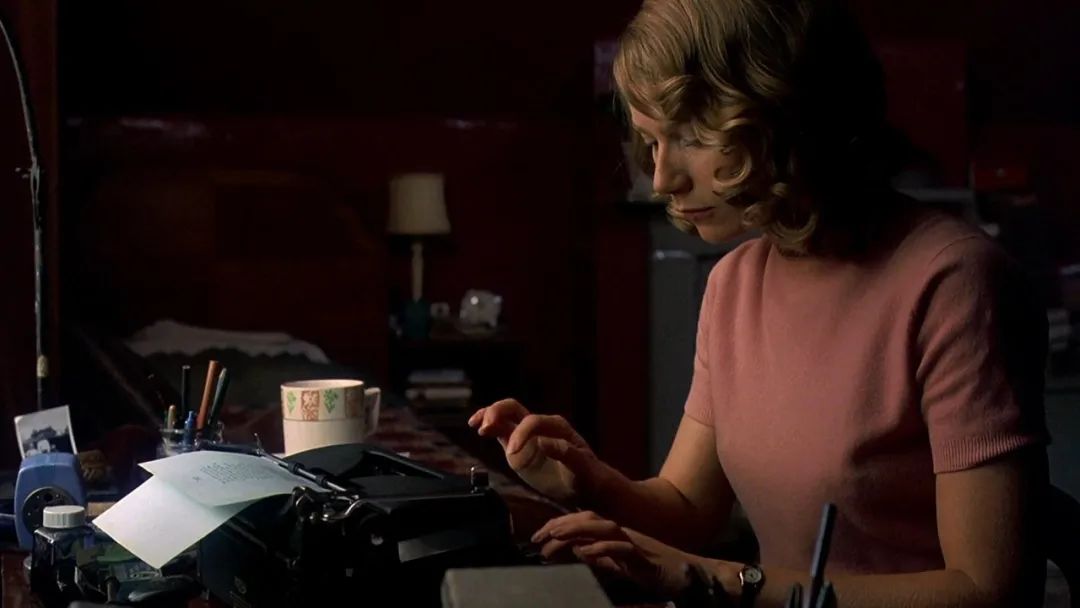
我变成了我的言语,
而言语也变成了我。
我是个作家,完全依靠语言来确立自我身份。我用语言工作,然而这堵墙总让我保持距离,把我隔离在外。这堵墙无法避免,不管去哪儿,它都四面围绕,以至于我开始怀疑,墙是不是我本身。
写作,是为了拆毁这堵墙,以一种纯粹的方式表达自己。写作的时候,外表和名字都无关紧要。人们在没有看见我的样子、没有心怀偏见、没有戴有色眼镜的情况下聆听这个声音。我是隐形的。我变成了我的言语,而言语也变成了我。
用意大利语写作时,我不得不接受第二堵墙的存在。它非常高,甚至更难越过:它就是语言之墙。但从创作的角度看,语言之墙不管多么让人恼怒,还是能够激发兴趣和灵感的。
——《墙》
该怎么定义这本书呢?这是我写的第五本书,但它也是一本处女作。它既是终点也是起点。它基于一种缺失和匮乏。从书名开始,它就暗示着一次拒绝。这一次,我拒绝接受那些已知的词、那些我本该拿来写作的词。我在寻找其他的词语。
我认为这本书既犹豫又大胆。它的文本既私密又公开。一方面,它源自我写的其他书。主题说到底并没有改变:身份、异化、归属感。但是它的外皮、内容、躯体和灵魂都经过了变形。
这是一本旅行之书,但我得说,它更多地是一场内在的旅行而非地理上的旅行。它讲述了一次连根拔起的过程、一种迷失方向的状态、一次探索。它讲述了一段时而令人激动、时而令人疲惫的旅程。这是一次荒诞的旅程,因为旅行者从未抵达她的终点。
这是一本充满隐喻的记忆之书。它讲述一场搜寻、一次胜利、一场持续的失败;讲述一段童年、一次成熟、一次进化,或许是一场革命;是一本爱之书、苦痛之书;它讲述一种新的独立,也伴随着一种新的依赖;讲述一次合作,也讲述一种孤独的状态。
——《后记》
*配图及封图来源:《弗朗西斯·哈》
《将来的事》《希尔维亚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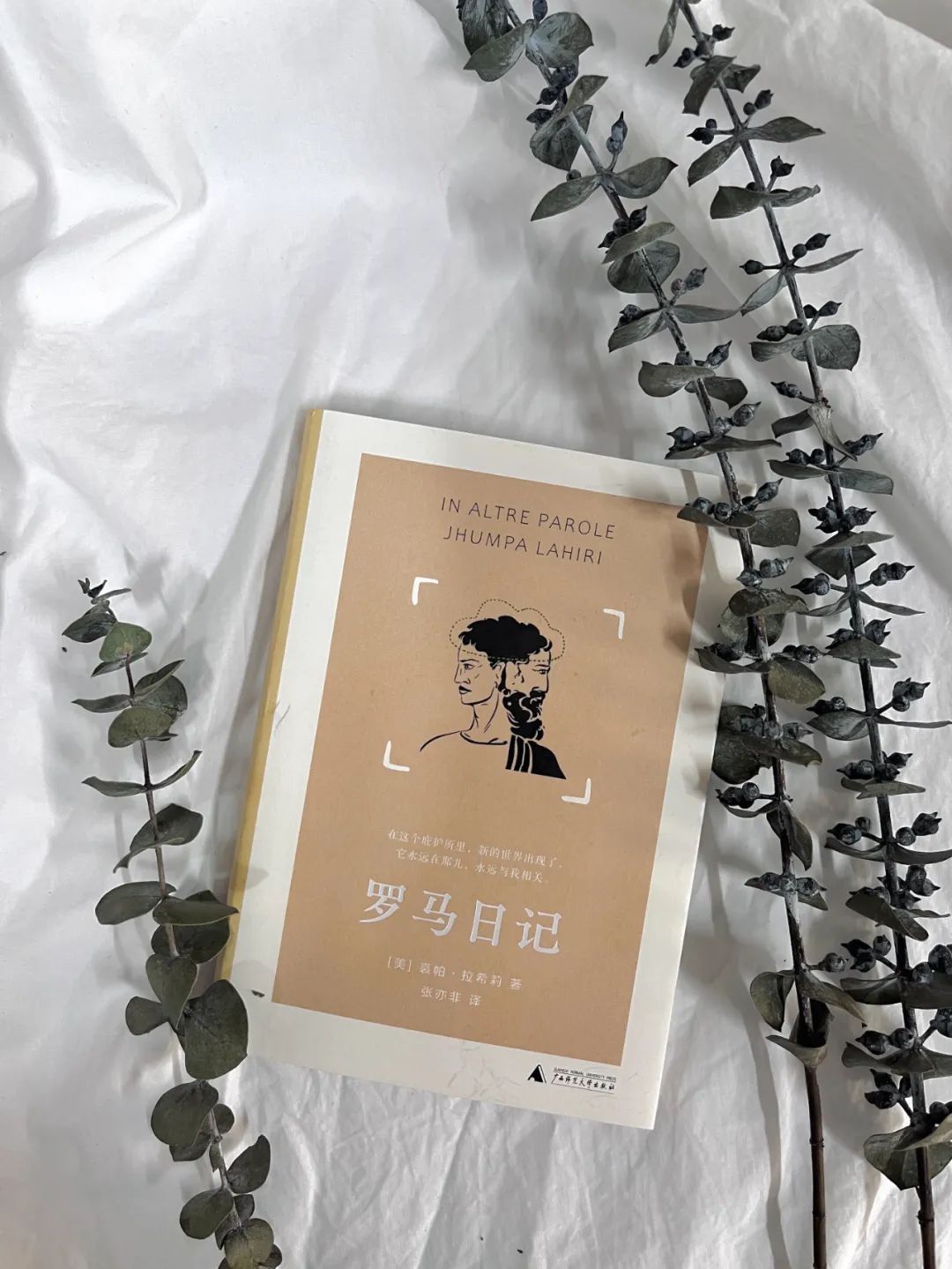
| 留言与评论(共有 0 条评论) “”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