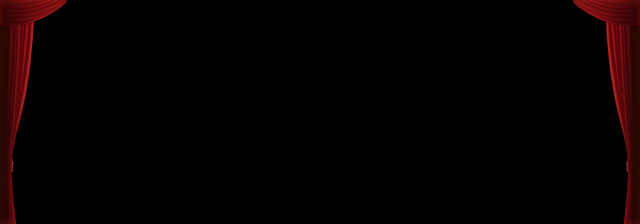
进入7月,已经有两个农村题材爆火了。
在最近被刷屏的B站短视频《回村三天,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》之前。

李睿珺的[隐入尘烟]也出乎意料的成为了一匹文艺片黑马。
它们确实属于相似题材。
意外残疾的二舅,没有怨天尤人,而是在村庄这一片小天地活出沉默又乐观的人生。
好人有铁不断辗转在屋脊推平的乡村,一边流浪一边还要给人供血。

李睿珺更在采访里,夸赞二舅比有铁“更能”,引用[一代宗师]的台词“人活一世,有人活成面子,有人活成里子。”
赞同他们都是活出里子的人。
作为农村失语的边缘人,获得大众关注,弥补了这部分题材在影像上的缺失。
原本应当是好事。
只是,当不知从何时起,大众舆论对农村题材的反馈,变为了:
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活出了我们向往的饱满人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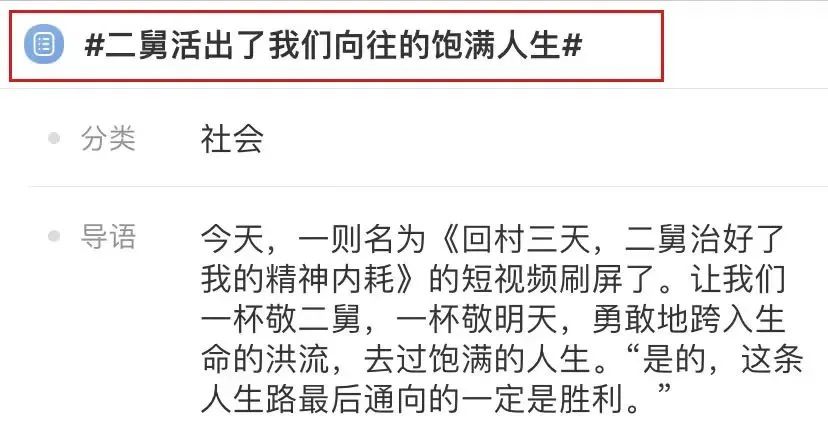
这种感觉就变味了——
怎么能把失语者的苦难,咂摸得如此有滋有味。
又用他人的苦难来获得自我治愈和自我救赎呢?
治好精神内耗活出饱满人生这一类话语包装的再好。
都不能否认,有对失语者人生苦难浪漫化叙事的嫌疑。
在这点上,我认为原作者衣戈猜想并不无辜。
他呈现好人好事的二舅、自强不息的二舅,包裹升华所谓二舅精神的动机。
明显比呈现与关怀农村老人生活与命运的动机来得更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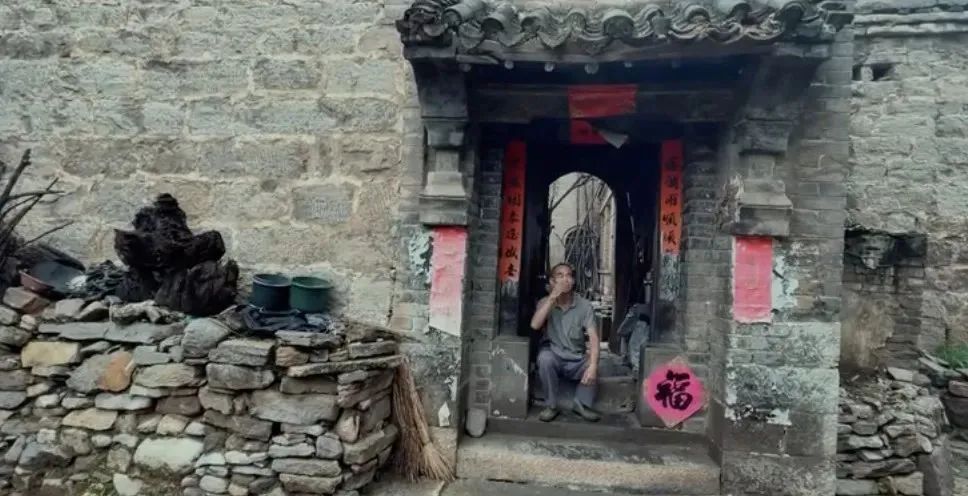
从标题上“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”主语为我开始,这一爆火视频,可能就与二舅不大相关。
而与我更直接相关。
于是,你看到说,二舅一生中的苦难——
天才少年因为庸医治坏了腿、残疾之后残疾证办不下来、拖着残疾的身躯做木工为生;
一生未婚并留守只剩老年人的农村,66岁带88岁的母亲一起上工干活......
被流水呈现完之后,升华致敬的标准正能量高度竟然是:
我四肢健全、上过大学,又生在一个充满际遇的时代,理应度过一个比二舅更为饱满的人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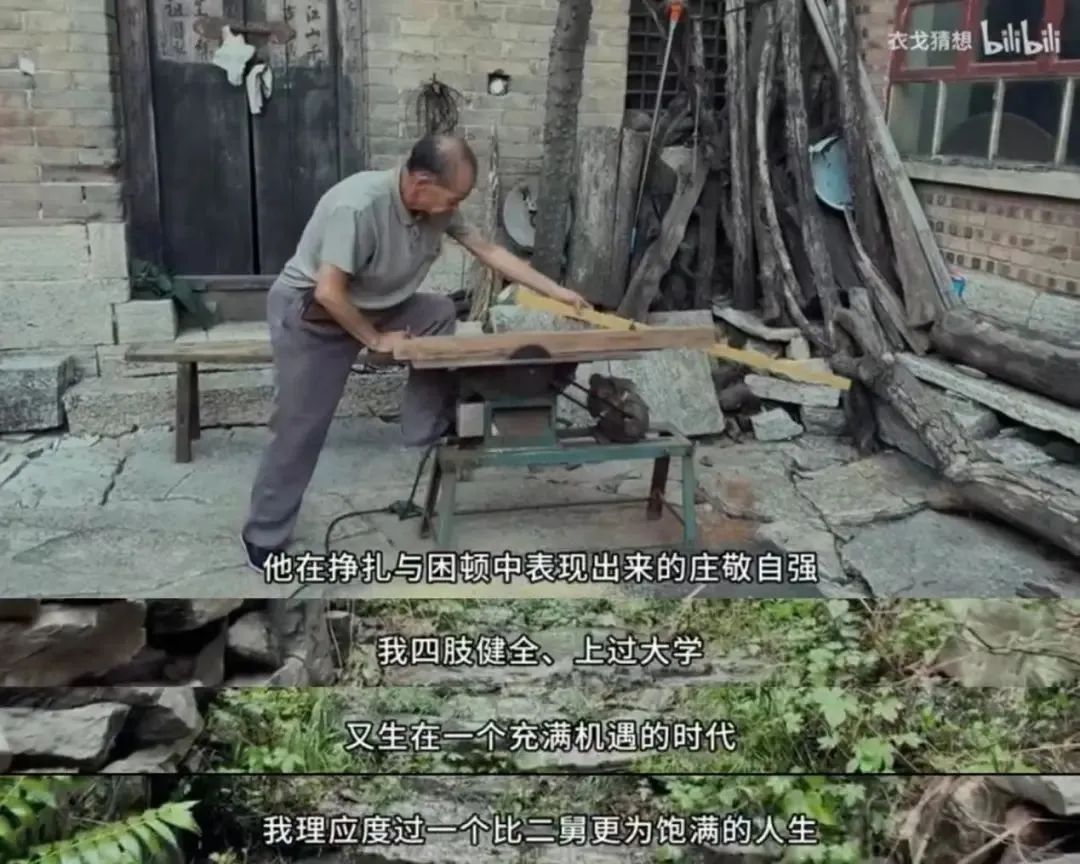
看客们跟着作者自我代入,一起感动流涕。
就有了将二舅精神升华到一个高度来自我勉励的心理治愈样本——
看!他多惨,但他多自强不息。
即使当下艰难,我们new generation又有什么理由emo呢?
二舅太惨了,惨到让人不适。
一生已经如短视频叙事中苦难一遭又一遭,还要被人拿出来细细咂摸、认真消费。
想起了另一个关于舅舅治好了外甥精神内耗的段子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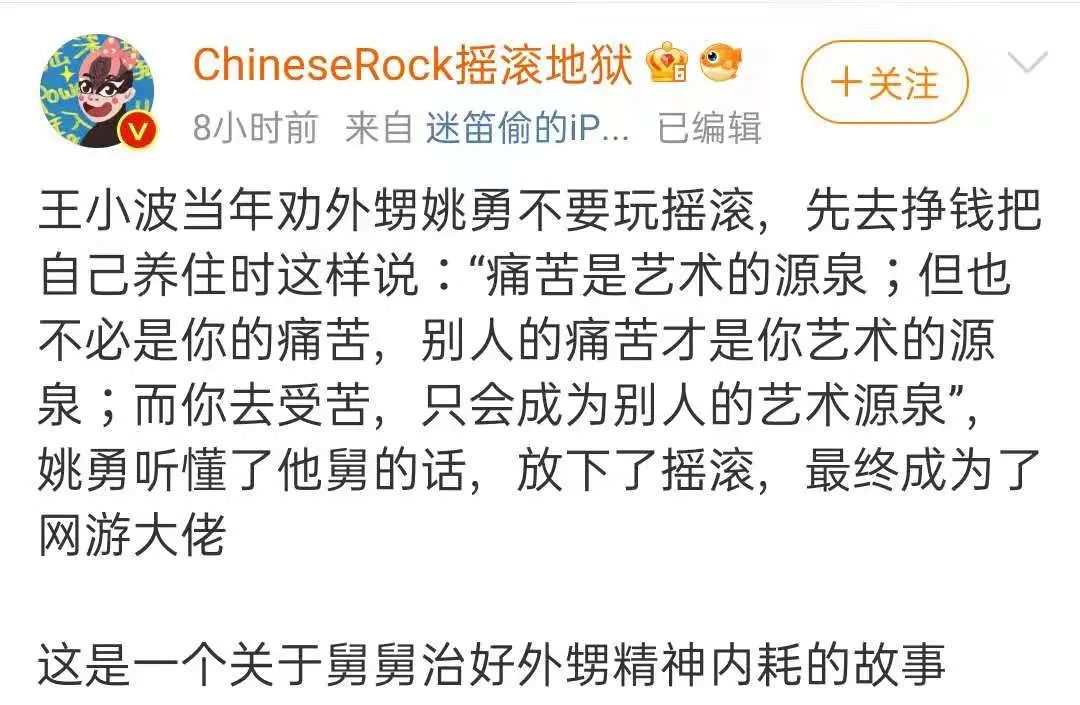
你去受苦,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,真实到让人想报警的程度。
而短视频中又是如何轻轻消解掉沉重的苦难的呢?——
比如,导致二舅残疾的医生。
故事的结局是:
有天二舅在路上遇到了当年的那个医生,他跟二舅说:“要是在今天,我早被告倒了,得承包你一辈子。”
二舅笑着骂他一句,一瘸一拐的又给人干活去了。
作者对此总结:
“这个世界上第二幸福的就是从不回头看的人。”

因为不回头看,过往历史的残酷现实——比如对当年事故的追问、赔偿、医疗问题,就能被一直遮蔽。
可要问的是。
这是二舅自己主动选择的生存哲学吗?
还是在现实无奈之下的不得以为之?
或者,二舅压根没开口说话。
这甚至只是视频作者自己理想中的自我投射和代人总结?
可能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:在这部讲述乡村失语者二舅的故事中。
二舅再一次被动失语了。
退一万步讲,即使不往回看。
去掉美好乡村的滤镜和糖衣包裹的文案,更值得关注和讨论的,也是视频背后的乡村当下现实。
比如,6688养老组合。
视频里说:
“66岁老汉随身携带88岁老母,这个6688组合简直酷得要死。”

66岁的二舅很想为自己多挣一点养老钱,将来就不用拖累养女宁宁。
但是88岁的姥姥现在的生活已经不能自理,也不是很想活了。
有一次甚至已经把绳子挂到了门框上。
于是,二舅木工活也不做了,全职照顾姥姥,早上给洗脸,晚上给洗脚,下午一起锻炼。
在采访里,当被问到二舅的收入来自哪里,6688组合日常生活又是靠什么维持时。
作者回复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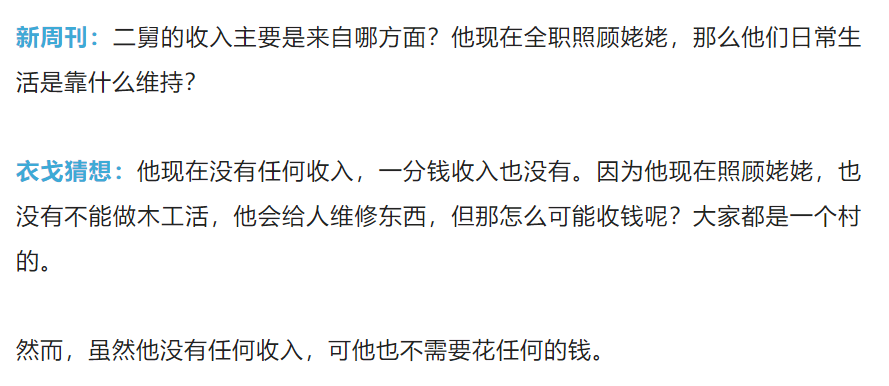
没有任何收入,一分钱收入也没有,全靠村民接济过活——
二舅给全村人修东西不收钱,村民就将吃的食物送来给二舅。
6688养老组合。
让我想起之前写过的日本NHK纪录片[老后破产]中的养老状态:
69岁的河口晃独居生活,但要每个月多次辗转去外地的护理机构看望97岁的母亲。
前往的路费,也是一笔巨大花销,他为此不得不找了一份驾驶员工作,赚点时薪。
同样60多岁的青山则选择独自在家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91岁母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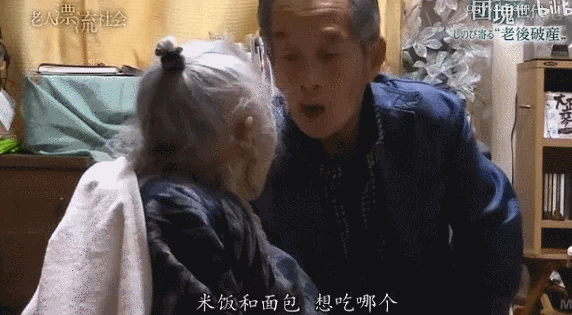
他每日计算着自己为数不多的养老金,紧张度日。在照顾上一代和为自己养老的夹缝里,艰难求存。
当年轻时存下的钱有一天用尽这么办?
一阵沉默过后,老人还是如实吐露:“可能会考虑自杀之类的事情吧。“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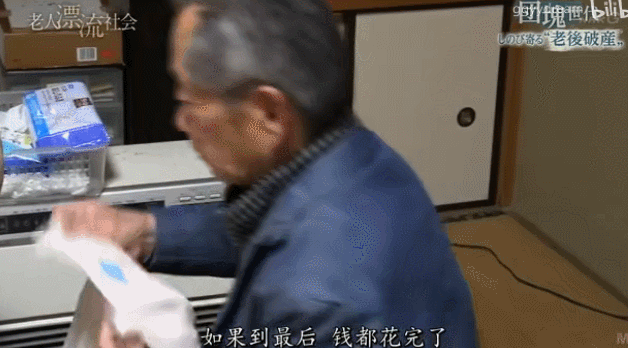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,看[老年破产]时,也很容易意识到。
生活在中国农村的老人们,只会比NHK镜头下曾经跻身中产、又老年破产的老人们境遇更糟。
周浩曾拍过一部独立纪录片[日子]。
记录了在冬天的四川达州农村,一对老年夫妻的生活。
斩猪草、泡猪食、喂猪,摘豆角;背竹竿、搭棚子,打谷子、背篓子。

用竹篾介赶鸡,用煤球碳灰敷在鸡粪上清扫地面。
他们很老了,不知道具体年岁,只是被压弯了腰和褪化了身骨。
每一次呼吸,都发出沉重的一声呻吟,他们日复一日,沉重又沉默的重复着相同的劳作。
这里没有年轻人,没有娱乐,没有精神内耗,也没有饱满人生。
只有偶尔一天某个时刻,一直沉默着干活的老太太突然叹息了一句:
“哎呀累得要死,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。”

而谈到自己孙子,老人则说:
“他可能再不会种地,以后只在城里买房子,不会再在乡村住了。
无论如何,他还是会说他的老家在这山沟里,他在这土生土长”。
梁文道在《圆桌派》里说:很多人的人生观就是活着。
想想视频里曾已将绳子挂到门框上的88岁老母。


那被轻轻带过的、被罗列展示的苦难中的一秒钟。
对这部分农村老人来说,只是活着,就已经用尽全部力气了——
而这时候,他们往往难以自救。
我们需要更系统的、制度性的扶助和变革力量给到乡村。
这也是对大众来说被遮蔽的、我们难以看见的另一面:农村,如同老人们一样,步履蹒跚。
以及,讲到这里,又想到视频作者的另一句名言:
“这个世界上第一快乐的是不用对别人负责的人,是树先生。第二就是从不回头看的人,是二舅。”

树先生一词,出自魔幻乡土题材电影[Hello!树先生],用来指代精神病人。
农村里的精神病人/残疾人/老年人。
作为最具失语症的一群人,当他们的苦难,成为一种景观,被正常人/年轻人/中产娱乐化、浪漫化定义为“快乐”。
这何尝不是一种话语权暴力?
即使身边没接触过真正的病人,但凡看过一眼聚焦东北某精神病院的纪录片[囚]。

都不会有人将他们被反复折磨、周而复始的清醒——疯癫的痛苦,定义为“无知的幸福”。
无论如何,生活在城市的新世代青年人的精神困境,值得关注。
但不应该以更边缘/失语者的苦难,作为治愈药引。
这太冷漠,太残忍,也太暴力。
最后,回到城市青年人的精神内耗。
或许,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精神困境。
当下的精神困境,我们生活于其中,太过了解,又因为一些原因,无法具体和深入谈论。
于是,只能借助于他人的故事来自我投射。
火的是农村的二舅也好、城市的三伯也罢,最终,城市青年人看到的是自己。
但也因为将别人的苦难消解为一种正能量的鸡汤叙事。
这种所谓的“治愈”,又如同挥拳打中棉花一般无力。

因为,它终究不触及我们切实的困境——
甚至,明明是当下外界现实的困境,却转而被简单化为一种个体的、情绪的、心理的精神困境。
即使是李睿珺的[隐入尘烟],走入影院,获得了两个小时的共情与感动体验。

可是,走出影院,那之后呢?
像有铁一样时时隐忍?
像二舅一般淡然忍受?
这般,精神困境与现实难关就都被治愈好了?
要是这样,那也行吧。
毕竟我们一向擅长于自我规训,自我和解,自己看个《二舅》文学,就把自己准备好了。
继续驴子拉磨,努力奉献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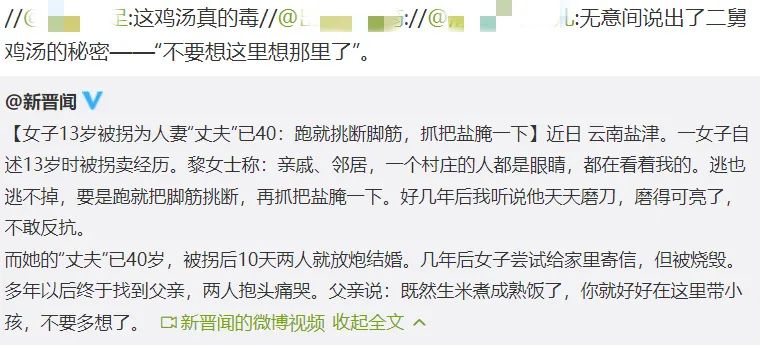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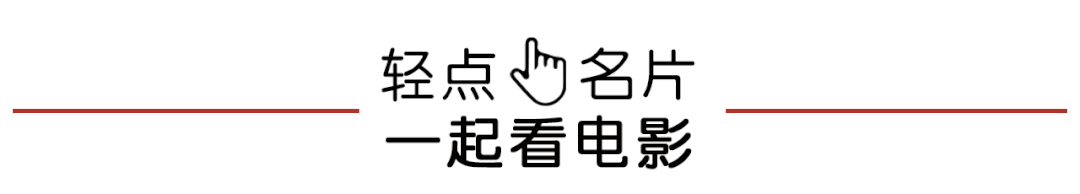




| 留言与评论(共有 0 条评论) “” |